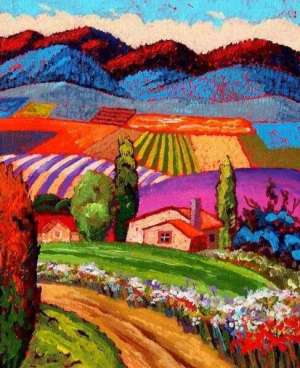朝鲜时代文人养花从禅僧清玩到全民赏蒲美在
文|葛星 编辑|赖丹蕾
石菖蒲文化在日本的第一次勃兴,大致在镰仓时代。倘若往前追溯,只能是依稀可见石菖蒲的草蛇灰线。
描绘平安朝(794~1192年)贵族生活的绘图《春日权现验记》中,绘有置于青瓷盆中的小型植物,据日本学者考证可能为附石菖蒲。然而在华丽璀璨的平安朝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日本文学巅峰《源氏物语》还是贵族和歌,都没有留下关于石菖蒲的记载,可见此时纵然有种植石菖蒲,也并未上升到文化审美的高度。
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当时中国(唐朝时期)的石菖蒲文化还没有传至日本。当然,这不是说当时日本就没有野生石菖蒲。只是在交通运输以及栽培技术都不甚发达的当时,连担负振兴国家重要使命的往来使节与僧众,像是求法的空海(日本遣唐高僧)和传法的鉴真,往往都要面临九死一生的渡海之行,要完全靠海路来"进口"石菖蒲,当是不现实的事情。
也许,当时承担着中日文化交流主力的遣唐使和留学僧人还是比较专注学习工作的吧,他们的"玩心",当真比不过接下来的时代要登场的"同行们"。
宋代禅僧:我们不生产石菖蒲,却是石菖蒲的搬运工随着历史前进到武家政治的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年),与之前主要由日本僧侣来"取经"不同,这一次,幕府统治者们从中国延请了一大批禅僧到日本开山建寺。
以宋代高僧无学祖元等为代表的大批僧侣东渡,为的当然是传播佛法。不过,有意无意间,这些渡日的禅僧,也将自己的个人爱好带去了日本,附石菖蒲就是其中一例。对比"心无旁骛"的唐朝留学僧们,开句玩笑说,"派遣员工"和"高薪聘请"的,待遇真的是不一样。
禅僧为何喜欢石菖蒲?且看与无学祖元同赴日本的镜堂觉圆的石菖蒲诗:"碧玉盘中水石间,根蟠九节剑铓寒。清标富足萝窗底,三屿十洲谁共看。"
正如唐代诗人常建歌咏的"清晨入古寺"、"禅房花木深",人间草木,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片风土,总是能轻易勾连起人们对于自然山林的亲近感,禅僧也不例外,甚至其感受性更为敏锐。而一盆清水,一拳附石菖蒲,又能教人联想到"三屿十洲"的大千世界,这自然又是"芥子纳须弥"的世界观。
另一方面,石菖蒲又承接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文明的憧憬。那时的宋朝,石菖蒲早已经成为了文人雅士们的钟情之物,从歌咏"雁山菖蒲昆山石"的陆游到写下《石菖蒲赞并叙》的苏东坡,这些中华文化的"大V"们的咏蒲之作,对敬仰中华文明的日本上层阶级与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就是石菖蒲文化东传时最好的背书了。
因此,当时日本人赏玩石菖蒲的方式主要是将附石菖蒲置于青瓷盘中清玩,与中国宋朝的清供意趣别无二致。这种附石菖蒲,甚至成了贵重的礼物,无学祖元曾作诗《太守送菖蒲石》云:"一峰寒浸碧琉璃,浪打枯严水半欹。仿佛去年天海外,客帆初到博多时",记述的就是幕府统治者北条时宗以附石菖蒲为礼的故事。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禅僧的菖蒲诗中,甚至还能看到"艳诗",比如后代名僧横川景三就写过这样一首诗:"绿水白沙天一盂,始知春色在菖蒲。九花持赠美人侧,留得鬓云长可乌。"
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这位风流诗僧与一位美女的香艳交往,然而实质上,却是身处短暂和平时期的禅师对于世相的感叹,此中意味,与宋僧圆悟克勤"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倒是有几分相近了。
从茶道到书斋:横跨东亚的"大IP"诞生记禅僧们的本职毕竟是修行。镰仓禅僧、文学的佼佼者虎关师炼,虽然在其名作《盆石赋》的开场第一句就写自己从少年时候起就是附石菖蒲的拥趸,然而到中年的时候,开始感到贪玩而荒废禅修的罪过,遂任由别人分而取之。
禅僧也许会因为佛法精进而放弃"好玩"之心,不过很快,"石菖蒲同好会"就迎来了又一批玩家。
此时,日本已经进入了战乱不断、人世无常的战国时代(1467~1585/1591年),讲求一期一会的茶人,在他们主持的茶会上常用石菖蒲和盆石来点缀茶席,既因蒲石的清雅之气,也因为它们承接令日本文化人士向往的中华文明。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的茶道笔记《山上宗二记》里,就留有"石菖钵"等名品的记录,还记有"子庭石菖蒲之绘",此处"子庭"即指元代僧人柏子庭,可见当时非但石菖蒲可以成为茶席上的陈设,连绘有石菖蒲的画卷也是布置茶室的佳品。
战国之后,日本进入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增长迅速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除了茶人之外,受到中国明朝文人文震亨、屠隆等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文人画的东传,石菖蒲也逐渐成为了日本文人的案上伴侣,清供佳品。
江户时期著名儒学家那波活所,曾写下长篇汉诗《石菖蒲赋》,其中有佳句"络石而自荣兮,贯四时而酷苍。且筛东轩之日影兮,含西窗之风凉。汲寒泉而一溅兮,何其清气而余香。"此赋中又历数中国炎帝、汉皇乃至修道人安期生、梅子真与石菖蒲的典故,可见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知识分子的浸润之深。
不独如此,随着东亚大地的交通日渐发达,文化交流的昌盛,石菖蒲还成了不折不扣的"跨境网红",贯通中日韩三国文人共同的趣味。十五世纪朝鲜的姜仁斋景愚著有《菁川养花小录》,不但介绍石菖蒲的莳养方法,还记录了苏轼、谢叠山、诗僧参寥等人的菖蒲诗,以及日本的石菖蒲趣话。
至此,历经禅僧、茶人和文人的追捧与赞颂,石菖蒲已成为日本中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文化活动中的文化标志之一。而另一方面,自江户中后期始,勃兴的石菖蒲文化也吸引了商人的目光,进一步推动了石菖蒲的大众化乃至商业化。
庶民化的石菖蒲:江户时期的"蒲疯"与没落商业化是石菖蒲东传日本八百余年中的最后一次变革,由俗到雅,进入到普罗大众的生活。
此时期描绘世俗生活的浮世绘中,就常有石菖蒲入画。另一个标志,是大量奇特衍生品种被培育出来,例如小型种、花叶种等。据记载,在文化三、四年(即1806~1807年)间,斑入乃至异形的品种,超过二百三十种。
在此商业化大潮中,有人因培养附石菖蒲而致富,比如1816年出版的《十方庵游历杂记》说,有一名叫伊左卫门的百姓妙用地形、善培养附石菖蒲,其它蒲商"无可出其右者",本人也凭此成为当地"首富"。
也有人投机取巧。十七世纪出版的《花坛地锦抄》里就记载有一种"龟子石菖蒲"的快速培养方法,乃是将培养土铺设于一种圆形素烧陶器里,并将石菖蒲修根剪叶,以竹签固定于此容器中。约五个月后,将陶器打碎,受其形状所限,此时石菖蒲呈团形,盘根错节,翠叶通透,其形则如小龟,故名"龟子石菖蒲"。
还有一些商人甚至作假牟利,用竹钉将蒲根钉在一起,这样一夜之间就可以造出"龟子菖蒲"来。这种赝品往往是卖相极好,清早拿到市集上去专门卖给不太懂行的"初心人",然而带回家后,一天不到石菖蒲便枯死了。
江户后期的这场"蒲疯",自十九世纪初开始,持续了二十多年,到1828年,石菖蒲的价格升到顶峰,随后迅速盛极而衰。据《宝历现来集》记载,自该年八月开始,到十二月,不过短短数月,蒲价就一落千丈,"看顾者一人皆无也"。
乡土研究者伊藤隼在1935年出版的《东京植物物语》里也说,在江户的三鹰地区有地名叫大泽,曾是著名的附石菖蒲产区,然而到了1932年,作者再访大泽时,却是一家店铺也见不到了——"惟见清水之中,叶略宽大之石菖蒲及小叶石菖蒲两种依然在目,仿佛诉说昔日往事。"
对伊藤隼的这番描述,经历了过去两三年间中国的菖蒲热与退潮的我们,当是心有戚戚焉的吧。
总 编 | 邓雪松
主 编丨林育程
执行主编丨程香
资料来源 | 《美在中国》2019年8月刊